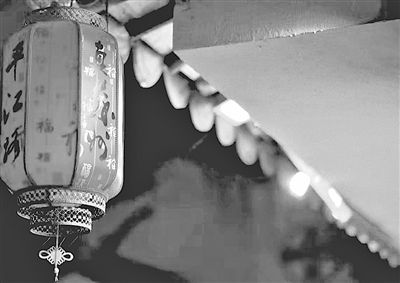
静谧。摄影/陶必福
◎谢金陵
擦黑赶到车站,电子屏幕显示要晚点将近一个小时。本来就是慢车,晚点就显得更慢。
又等了很久才进站,夜风凛冽中,直到温热的身体一点点冷下来,火车才不疾不徐、慢慢吞吞闪着刺目的灯光,喘着粗气哑着喉咙停靠在站台上。
灯光居高临下,清冷的白光睥睨着陷入瞌睡的慢车。它太老了,厚厚的绿漆遮盖不住铁皮的斑驳,沉重的车头印满苍黑的风霜。从黑洞洞的远方驶过来,深长的车身被拖行得颤颤巍巍。
相较于高铁、飞机,绿皮火车可以把行程拉长,走出古人用脚程丈量山水的诗意。坐在这样的慢车里,我总喜欢守在车窗前,让各种各样的风景迎上来,掠过去。车轮咔嚓咔嚓地敲击,车身吱扭吱扭地摇晃。你在时间之外,你在空间之中,在移动的慢车里,你是行走的本身。
此刻,夜色中的慢车开始缓缓行进,钢轨与齿轮承合,黑暗和灯火交迭,徐徐拉开的焦距中,光与影不断铺在身后。
颇有年头的立交桥横亘在新建设的小区和待建的废墟之间。当年先进的设计,到如今显然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橙黄的灯带烛照着敦实的桥身,光线迷蒙,穿过桥洞,填满欲说还休的怅惘;古老的沱河水被冰层噤了声,折射其上的七彩灯光和真实的灯火交叠变化,衣袂飘飘,光影绮丽,托舞出一场寂寞而又盛大的人间幻境;公园掩映于枝条剪影中,地灯上射,疏影横斜,意态阑珊;两边长长的路灯加持着盘旋的公路,迤逦婉转如飞天的灯河;迎上来的楼群被灯光温柔了每一扇窗口;坐落于郊外的厂房藏匿了忙碌的通宵,围墙深处,灯火通明;而在无边原野,灯光逐渐寥落,黑暗逐渐盛大……
灯光是城市的第二张脸,和在自然光线中呈现的那个世界迥然不同。他们过滤了不想呈现的地方,他们勾画了应该浓墨重彩的部分。他们驱赶着黑暗,消散着黑暗,同时又利用着黑暗,描绘着黑暗。
移动产生距离,距离产生美。小城是熟悉的,因为司空见惯,所有的美早已习以为常。但在移动的慢车上,辞别使窗外的景物意味深长。这座我谙熟于心的城市被各种各样的灯光所包围、所辉映,同时它又被或深或浅的黑暗所衬托,所托举,像是梦境给现实镶了边,把平淡的城市变得艳丽夺目、光彩非凡。
在城市深处,那些密集的、璀璨的、烟花一般的灯火盛开在车窗玻璃上,不断绽放又不断被抹去,制造了一幕幕流动的视觉盛宴;而在深深的旷野里,夜色吞噬掉所有的光亮,无边无际的黑暗低伏着身体跟随着列车向前延展。
无论灯火是热闹的,还是寂寞的;是盛大的,还是稀疏的,是亲近还是遥远……在缓缓行走的暗夜车窗上,都美得让人忍不住暗暗地惊叹。当所有的光芒收去,车内的灯光落在窗户上,像是在你的面前竖了一面镜子。而黑暗,则在窗外立起了一道墙。
此刻,我凝视着玻璃里的映像,她和自己并肩而坐,和黑暗一起并行,和铁轨一起穿梭。窗外的黑暗模糊了她的五官,窗内的光线虚化了她的轮廓,静止在车窗上的面孔既真切,又空幻,好像倒映在岁月深处的一个影子。
惊动和打破这份梦境的,是车厢里的灯光和身影。那些惯于被各种面具遮挡的面孔演绎成车窗玻璃上的风景,在镜面里或坐或卧,或交谈或打电话,我可以看清他们的每一个细微表情,每一个轻微动作,他们真实上演着自己并不知晓的哑剧,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偷偷地观察着他们。
而我何曾知道自己的背后是否驻留过目光,另外一面的玻璃深处,是否也会有一双眼睛对我暗暗地审视?我们的面孔向外,我们的灵魂向内,像一扇在黑暗中行走的车窗,只有光亮能够短暂地洞穿。
年轻人是不喜欢坐慢车的。与高效整洁的高铁或飞机相比,慢车像老牛拉破车。有历史年头的车厢,相对拥挤且陈旧的空间,还有参差不齐的人群……慢车似乎意味着落后、陈旧、效率低下。年轻人急不可耐地成长,急不可耐地和青春抢时间。凡事讲究效率和成本,金钱就是时间,时间就是资本,它盈余出来的部分可以创造出比车票更高的价值。
慢车接着地气,更为亲民,适合不太讲究精致生活的人,出于价格上的考虑,收入不高或时间相对充裕的人群是它的主体。曾经处于城市繁华地段代表进步和文明标志的火车站虽然仍占据在原来的位置上,但已经被快速崛起的新地标孤立和碾轧。在更广阔更年轻的规划空间里,专门为未来开辟的高铁车站和航空楼更迭了它的历史。
所以,喜欢乘坐慢车的人一定是拥有岁月体验的,在相对迟缓的速度里慢慢回溯和深入时间的光影之中。
我已经到了应该慢下来的阶段,在时间相对充裕的情况下,我愿意乘坐慢车缓缓向前走。身外的一切都在风风火火地朝前运行,我可以保持足够的笃定,坐在车窗前,和身外的风景拉开距离,让他们远远地印在我的眼睛里,我的心情随之起起伏伏,却绝不大动波澜。时间的河流从来不是笔直地奔涌向前,它就像这外面的移动空间,或缓或急,遵循自己的规律,拥有存在着的道理,只要落进你的视线里,他们便都可成诗成歌。

